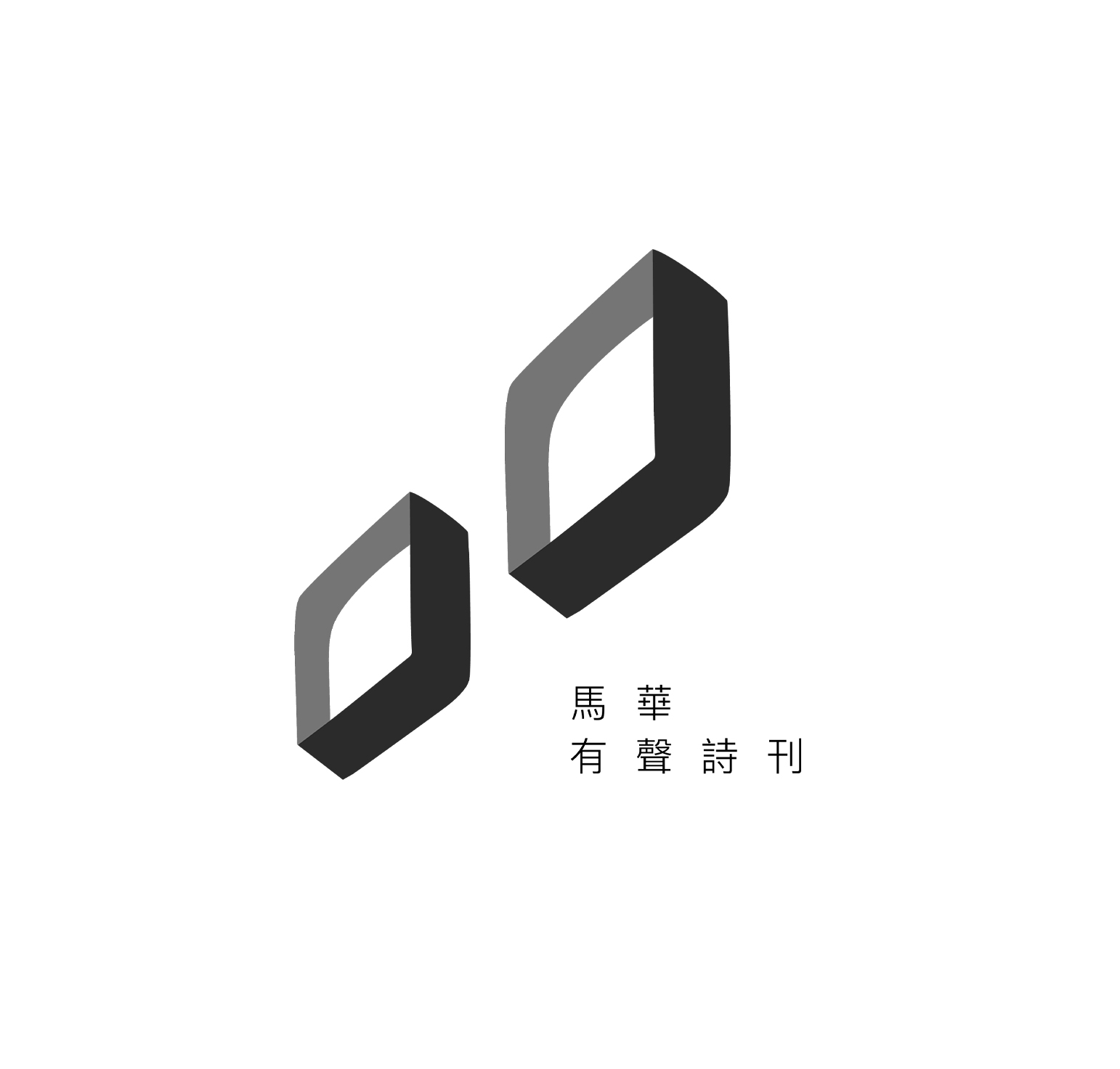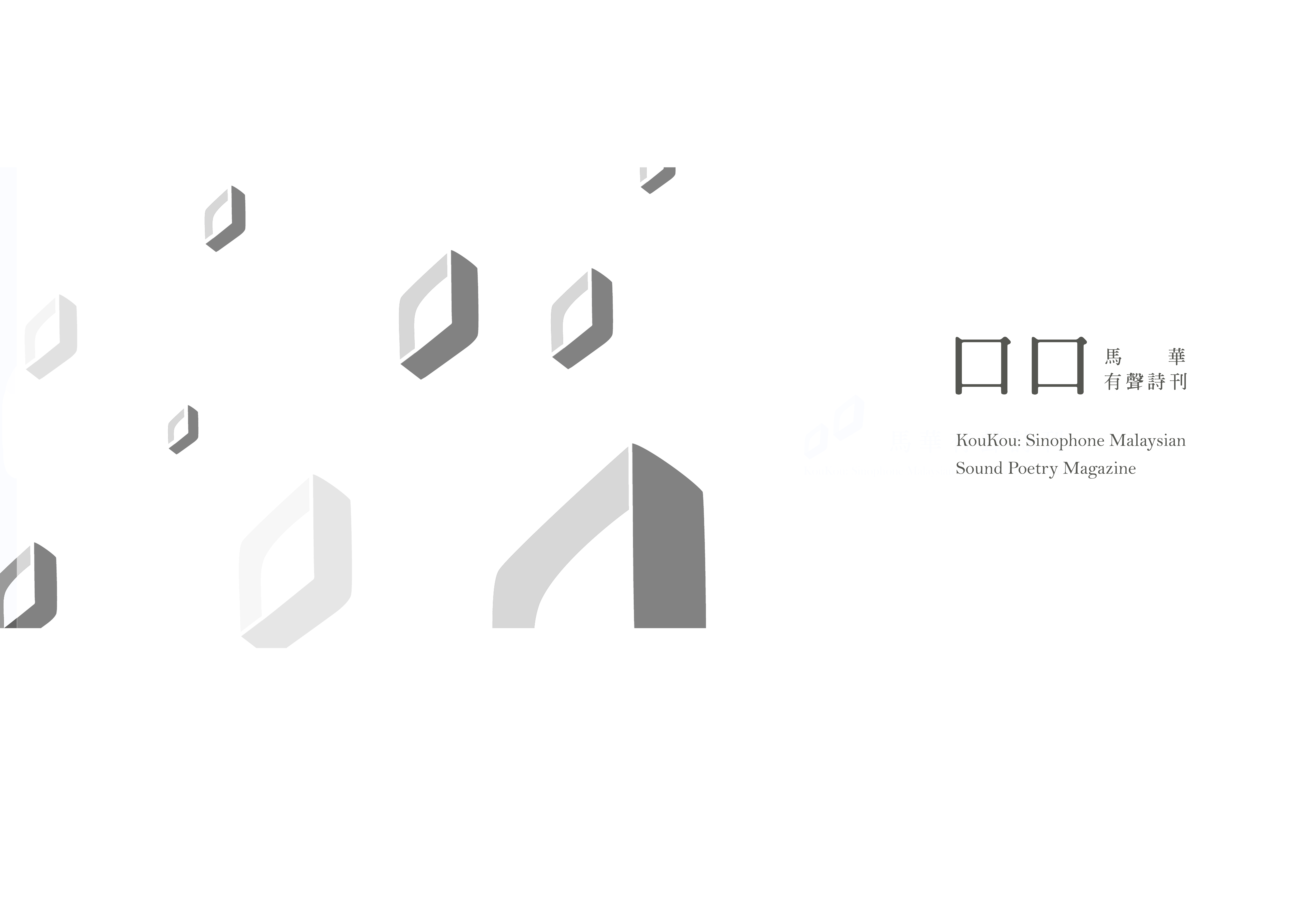有聲詩刊 Sound Poetry Magazine
當我們高談文學,想到的是的字裡行間的曖昧遊移、是主詞在冗長的子句中透露出的一點深意,而細細想來,這些精神的愉悅與探索無不出自於黑壓壓的文字;當我們談及文學刊物,腦海中浮現的往往是一本書。一摞摞的紙、款款大方的封面、賞心悅目的排版,還有那少不了的漫漶字符。但,書是為何物?時代驟變,再固執如書,近年來也不得不改頭換面,去紙質古法,換上「電子」新裝,以因應變化。輕便了、環保了,多了一副眼鏡了。縱使如此,遠古的精神探索與智力遊戲,仍牢牢套鎖於那無盡深淵的黑色文字鑰匙之中。書的本質不改,人們習慣犹在。
誠然,我們是得益於文字的。這一點,我們無法否認,更毋需矯情——因為我們都吃了文字的瘪。上癮,名曰冰毒、K粉與文字。文字成了一種神秘的癮。很多時候,我們依賴文字的程度令人咋舌,甚至是忘了言語本身也未然察覺。只是,對文字依附成性無關天性,僅是文明與歷史的產物而已,因為文字乃歷史華麗的資產,卻也是爬滿白蟻且詭譎的古老文明病。「說故事人」(storyteller)未必就與文字難兄難弟;「口說傳統」(oral tradition)未必就流於落伍。在我們熟悉城市文明的另一端,數以萬計原住民仍以「口口相傳」的方式抵禦時間,傳承部落文明與「口頭文學」。在這個意義上而言,人無異於一本「書」。1877年,愛迪生「留聲機」降世,這是人類文明第一次通過技術保存聲音。從此,逝去的言語不再是上帝的藝術。文字記事功能的長期壟斷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。但是誠然今時今日,文字仍是文學僱傭的輕騎兵,更是「故事」的王。
如此,讓文學離開文字是否「永不」可能?21世紀數字技術時代的當下,我們是不是重新思索「書」與「文字」的關係何謂?以此作為思考的起點,《口口》不失為一個實驗性文學項目:作為一本「有聲詩刊」,我們希望鬆脫於書面思維之束縛,且讓文字退守次要位置,通過新媒體的聲景形式傳遞詩的「聽覺美學」(aural aesthetics),並亟欲探索「聲音詩學」(poetics of sound)與詩意(meaning in a poetry)之渊薮。由此,一時之間,當代的留聲技術與口說傳統,展開「新」詩的對談,以及那不該被遺忘的——無字天「書」的復辟。
數字馬華Digital Mahua
何謂馬華(文學)?无论是馬來(西)亞華文文學、馬來西亞華人文學,抑或近年熱門的馬來西亞華語語系文學,哪怕再有爭辯,“馬華”二字儼然業已成了某一範圍內不證自明的概念符號。於是,一個重要且關鍵的問題隨之而來——一個帶有馬華標籤的數字詩刊意味著什麼?這是否暗示該詩刊是由幾位年輕的馬來西亞華人在地所創?實則,我們幾位不僅身處空間不同,分別也經常流動於不同世界地理版圖,由島至島:吉隆坡、新加坡、北京、首爾、台灣,或更遠的地方。“在地”一詞恐成了虛設。那這是否意味著我們詩刊的作家群只限於馬來西亞人?誠然從文學史來看,有國籍的文學恐怕並非我們所擅長生產的文化產品。況且,在數字媒介的邊界含混性(boundary ambiguity)面前,一本詩刊的作家群身份還有多少意義?那這是否表明這本詩刊的讀者群主要面向於馬來西亞華人讀者?我想,這點倒毋需急於否認。但如果發生,這更多的是來自現實的傳統寓言,而非爾等追求的理想。詩無國界,數字無邊地,行駛在路上的車子會繼續往前,一路筆直,再看不到後方塵沙如何揚起,只是不知另一座城市的那棟屋子的陌生主人會不會在家。
如此,文學的生產空間轉為數字媒介,且超鏈接(hyperlink)成為新的邊界時——各地有興趣的讀者皆可隨買隨讀的情況下,詩刊上的“馬華”二字還存在著什麼意義?我想,重要的是,“數字馬華”成了嶄新的第三空間(The Third Space)。通過口口詩刊,人們數字寫作、數字購買、數字閱讀、數字傳閱(請自覺不要那麼做……)而成為了“數字馬華人”(digital mahua people),不問出身,以詩會詩。於是乎,“馬華”也未必需要拘泥於“族裔”與“國籍”,而是換上另一層身份的標準。換言之,無形的文化橋樑隨時建築、數字馬華社區沒有專屬邀請卡——數字使得“馬華”從只能執繩索兩端的固態之物變為來去自如的流體(fluid)成了一種可能。由於有聲性質,口口詩刊甚至不需要是一名傳統意義上的“讀書人”——只要“耳耳相傳”便可閱讀;“盲人詩人”也未嘗止於空談。
我們誠冀借以《口口:馬華有聲詩刊》重新思考並活絡古老而重要問題——何謂“馬華”,正如王德威在《馬華文學十四講》言道:“馬華文學的主體性永遠是與時俱進的話題,在不同時代、語境,就有不同的挑戰與因應之道”。所謂因應之道,想來,是如此這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