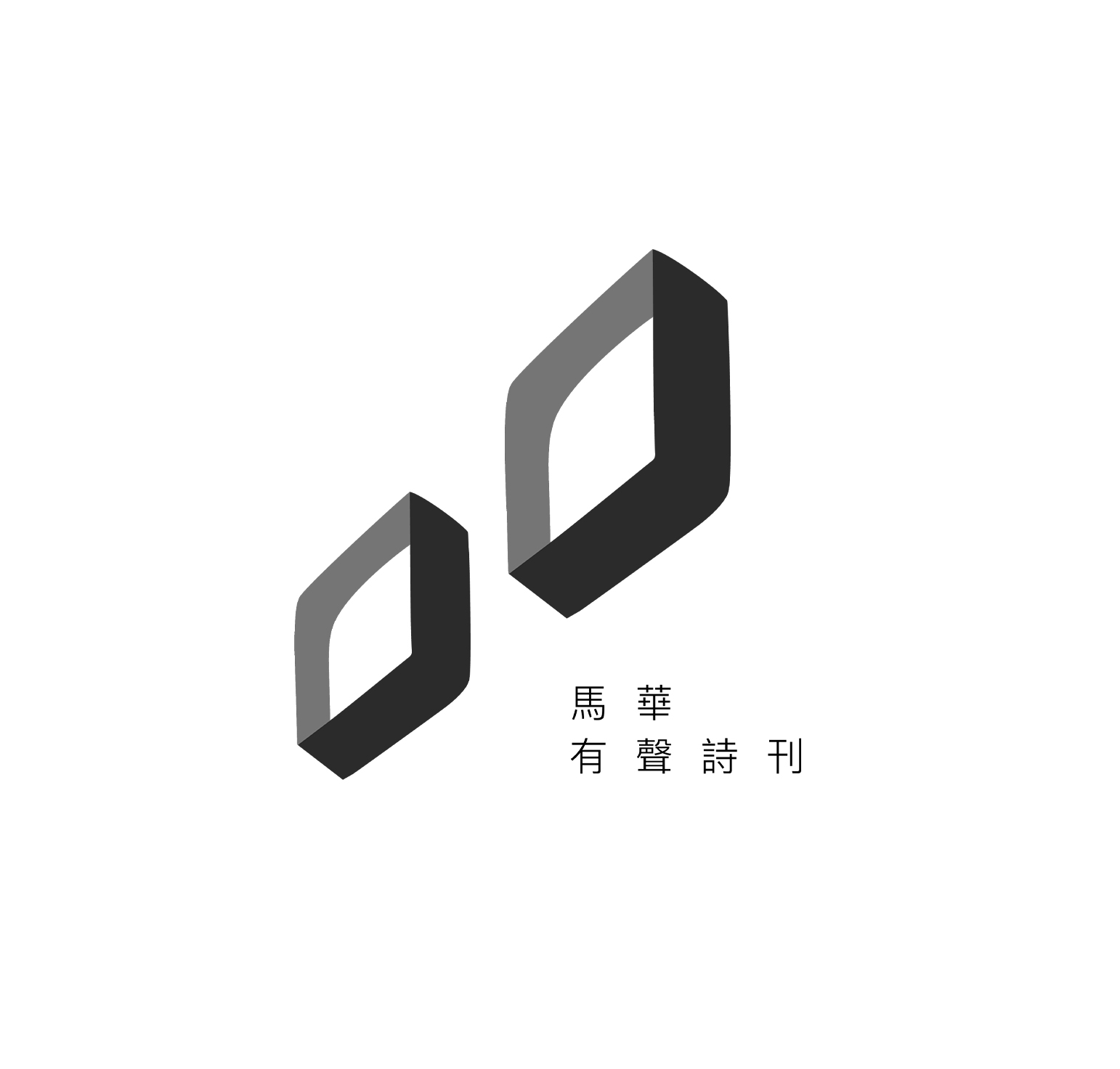第三期 Issue 3 / 翻牆——默迪卡!翻譯馬華 Breaking Through the Wall — Merdaka!Translating Mahua |
「如果牆是一種成見,是一種牢固的印象。」 ### 翻牆須知: 【詩人】 兩棲類動物,擅長變溫,時時分泌詩意的粘液,讓鮮艷的體表常保濕潤。 【詩歌】 上有暖熱的自然光,下有潮濕的土壤,井口生養這片溫床。 【翻譯】 寡聲寫下的詩,借助外頭的偶陣雨,或出處未明的地下水,讓久積的所有湧過高築的牆,浮上地表,也灌溉這片綠洲。 ——這裡並不枯癟,也並不只有空虛的迴響。這是詩人與詩的變態。 ____ 口口詩刊第三輯《翻牆》,以家國為主題,收錄了10首經過翻譯的馬來語和華語詩歌。讓我們一起翻過詩歌的高牆,走向遠方。 (關於牆的存在,我們不僅僅懷念它,我們還要打破它。) |
第二期 Issue 2 / 酷兒與流動 Queer In Motion |
——假使身體語言足夠表達所有的愛,我們由始至終才都不會願意把話,說得清楚明白。 因為沒有絕對的定數,所以適合碰撞不計其數的假設。因為沒有永遠的棲身之所,我們把自己寄放在世界各地。與生俱來的流動,促使我們練就變形的特異功能。最初是經由日常,揣摩著髮型、體格、膚色、樣貌、線條、品牌、氣味……將自身擠壓揉捏成他人所喜歡的模樣,而往往在最後,決定變成一件輕盈的、不被世俗定義的信物,可以無所重負地寄掛隨行,或者安心且靜地安於擺設。我們在現實的競爭中力爭上游的同時,也必須說服自己滿足現狀,例如對於善感身心的具體存在、身份的曖昧與待定、感受的生生滅滅、與他者的撞擊與分離。要是從來沒有身體作為展演的工具,我們還擁有什麼;要是沒有了書寫與詩作為裝載情慾的容器,我們還剩下—— /本期歡迎與「性别」或「流動」有關的任何詩作投稿。/ |
第一期 Issue 1 / 生態身體 Ecological Body
|
「你不需要把自己變成生態一些,因為你自身就是生態的。」(You don’t have to be ecological. Because you are ecological)(Being Ecological, 2018) 蒂莫西·莫顿(Timothy Morton)在書中最後一頁以此發人深思的句子畫下句點。當人們之間的談話每每需要觸及「自然」抑或「生態」時,我們總會掉入一個奇怪的情境的泥沼:我們談的「自然」似乎永遠是「非人」的,好像「自然」一直站在「人」的對立面——婆羅洲的熱帶雨林、神秘的貝加爾湖,或是非洲大草原;說起「生態」,一方面是想起某種「自然」法則呈現的平衡與寧靜,另一方面則可能想起「人」的種種行為的介入、干擾甚至破壞,結束了這份平靜。於是,不少人開始付出行動——吃素、環保、共享汽車,或是親近自然,窮盡了方法以減緩生態危機。類似的行動對人類世下的全球生態災難有所助益嗎?我想,理所當然。但若要說這樣就能解除危機,恐怕大家都清楚明白一點都不現實——因為「人」的集體行動極為困難。 而追根溯源,這還是出自於我們對「自然」與「生態」的理解——「人」是「包括在外」的。哪怕這個時代的綠色教育越發受到重視,而我們越來越付出行動去愛護自然時,我們身上像是裝了個「生態」開關——只是有些人把閘門打開得更頻密,有的人甚少去碰而已。或許,為了「人」的集體行動能夠發生,正如莫頓提倡,我們應該放下「人」/「自然」的舊式觀念,以重構對於「生態」的想象——我們大可卸下那個讓自己更趨近生態的開關,因為我們就是生態的。縱使可以使人們減少焦慮,莫頓的顛覆性生態思維倘若用在早已習慣接受規訓的一般人身上,吊詭地反而多少帶有一點理想主義,效果或許還不如一次迫切的生態行動號召。然而,放置在「藝術」的領地,情況便大為不同,其性質似乎是相呼應的——或許是因為它們皆「一無是處」,而「無用」的思考就是對「生態」最好的積極行動。「人」沒有「與眾不同」,而是「生態」其中之「物」——從科學而言,人體本來就是「人」、「微生物」以及「非生物」共存的生態圈。換言之,「人」自身即是一個生態的場域,與地球生態連著同一條血管,存亡與共。在生活中,睡覺是生態的、運動是生態的,人之交際亦是生態的——戀愛是生態的,連吵架也是生態的。 如此,「寫詩」與「讀詩」何嘗不是生態行為——在共存之下,一種恰如植物緩慢「生態身體」的反射動作。我們以靜制動,仗以「寫詩」與「讀詩」本身作為行動,追索自身與其餘萬物之間的關係——「人與人」、「萬物與萬物」的「周遭小生態」、「中生態」抑或全球共存的「大生態」,為「生態關係學」(ecological as relation)給出應答——或捕食、或競爭、或共生、或寄生、或無關共生,又或更多問題的提出。由此,本期詩刊,從「生態身體」出發,向詩人拋出橄欖枝,以詩應答—— 一、從「生態」的思維重新思考自身與周遭的關係,或是處理目前遇到的困難與煩惱:小至自我關係的「身體生態」;中至與他人關係的「情感生態」;大至與地球對話的「綠色生態」。 二、「人」作為生態一員的「物」,與其他「物」的平等關係。 三、「詩」(寫詩、讀詩)與「人」、「小、中、大生態」之間的關係。 四、從自身與周遭的關係,以「詩」的方式,詮釋自己對「生態」深刻的新理解。 |